中国人如何观察世界,可能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题材
- 推荐阅读
- 2020-07-18
- 226
题图来自受访者,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依蔓
2011年初,南方报业《南方人物周刊》旗下的人文旅行杂志《ACROSS穿越》创刊,当时在《南方人物周刊》做记者的刘子超和几位同事一起前往印度。他的任务是为新杂志的创刊号写一篇封面故事。
那时大家还对创办新杂志抱有极大的乐观情绪。相比起单纯的人文类杂志,旅行杂志因为题材的天然优势,在吸引广告或赞助方面应当不成问题。于是4、5个记者被派到印度,公款旅行40天。这样奢侈地扶持文字内容生产,在如今是完全不能想象的。
抵达南亚后,每个记者都有各自计划的路线,刘子超的目标是“佛陀之路”。从佛诞地尼泊尔出发经陆路进入印度,一路探访佛教记载中佛陀释伽牟尼慈悲度众的圣地,比如蓝毗尼园、菩提伽耶、鹿野苑、舍卫城、曲女城、王舍城、拘尸那罗、灵鹫山。佛教是大部分中国人对天竺的第一印象。
但行程刚开始10天左右,刘子超就在尼泊尔遭遇了一次交通意外。
一段喜马拉雅山地中不太平整的柏油路,一侧是山体,另一侧是地势下陷长满草树的沟谷。第一次骑摩托车的刘子超在行驶四五十公里之后有些疲累,一个拐弯没注意,连车带人侧翻摔在马路上,人因为惯性飞滑出去。他清晰听见自己的头盔在路面上一面撞得咣咣咣一面刺溜的声音,裤子磨破了,脚踝血肉模糊,疼得根本爬不起来。路过的当地人发现刘子超,扶他到路边坐下,还跳下马路另一侧的斜坡采了些药草,嚼出汁来给他紧急敷上。但因为还要把摩托车带回城里,刘子超拒绝了当地人让他坐大巴离开的提议,继续待在路边休息。
再次停下的是一辆小汽车。三个年轻人从车上下来,看刘子超的状况不太好便提出把他稍回城里,由他们其中一人骑着摩托车跟在后面。路上闲聊刘子超得知,这三个年轻人在尼泊尔开了一家私人戒毒所,主要业务是把当地的吸毒青年“绑”到山里,再向他们的家人索要戒毒治疗费,一种在灰色地带游走的“绑票”。而刘子超坐的车,就是他们平时用来“绑”人的车。为表感谢,刘子超按国内标准大致估算了费用,付给他们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的路费,抵得上他们“合法绑架”业务月收入的一半。
回到镇上后,那几个尼泊尔“绑匪”送刘子超去诊所处理伤口,又帮他修好了摩托车,还给车行。刘子超甚至还跟着他们去镇上一户人家,看他们如何告知穿着传统纱丽的母亲,“你儿子吸毒,现在在我们手上。”
这是9年前刘子超印度旅行的奇幻开场,开启了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以写作为目的旅行。
40天的行程结束之后,刘子超回到北京,用一个月的时间写完《ACROSS穿越》的创刊号封面故事,《车轮上的国度:穿越印度的火车之旅》。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录在刘子超去年出版的第二本作品集《沿着季风的方向:从印度到东南亚的旅程》中,同样是作为开篇。
文章的末尾,刘子超写到一位印度教徒对他说:“生命是一场幻觉。”这句话让他觉得可以停止对外来或往事的忧虑,因为“聚会是为了告别,到达是为了启程。”
到达是为了启程,也是作为一名旅行作家在路上的意义。

孟买的出租车司机

在印度时喝大扎翠鸟啤酒
一
在成为旅行作家之前,刘子超有好几年的时间感到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可以写什么。
2007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后,从小在北京生活的刘子超来到广州,加入《南都周刊》。南方报业是那几年对媒体有向往的学文年轻人的首要求职目标,如果他们不去国外读东亚研究的话。
入职之后新人们立刻跟着编辑们开选题会,有编辑和刘子超说,要不你去旁边工地和工人一起住,看看有什么可写的。南方报业位于广州大道中289号,目前已是非常繁华的地界,隔着江对面就是小蛮腰广州塔,但十几年前还是工地和城中村。刘子超去工地门口转了一圈,觉得可能挖不出什么东西,还是要自己找选题。他看到一条深圳城中村拆迁过最牛钉子户获赔1700万元的新闻,决定去采访试试。
背后的故事让刘子超也感到意外。
新闻里的“最牛钉子户”叫蔡珠祥,家里一直拮据困难,1972年妻子怀第二个孩子时,蔡珠祥偷渡到香港打工赚钱,几年后又偷渡去了南美,和家人彻底失联,在当地结婚生子。1988年,蔡珠祥听华侨说深圳已成为经济特区且发展不错,于是辗转回国,没想到妻子仍未改嫁。回国后的十几年里蔡珠祥和家人拆屋改建,把房间出租给不断涌入的外来打工者,每个月坐收租金。再后来就是遇到深圳老围片区的拆迁安置,变成千万富翁。
偷渡、改革开放、城市改建、拆迁,中国近数十年的时代变迁浓缩在一个小人物的传奇人生上。
这个故事刘子超采了一星期,很快写了出来,7000字。编辑没怎么修改,他当月就拿到了报社里的好稿奖。接下来的三篇稿子,刘子超又都拿了好稿奖。一切过于顺遂,刘子超反而觉得好像突然失去了方向。尽管大学期间刘子超很明确自己毕业后要去当记者,他印象中海明威似乎说过,你想当作家的话,有几年记者经验是非常好的。
高中时,刘子超考入北师大二附中文科实验班,班里的文学氛围浓厚,他开始大量阅读国外现代作家的作品,托马斯·沃尔夫、雷蒙德·卡佛、海明威、卡夫卡。同学们也会写小说,彼此交流,他们还自费在出版社出了一本收录每个人作品的作品集,取名《离海不远》。高二那年,刘子超参加了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以一篇借鉴詹姆斯·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题目灵感的作品入围决赛,获得第二名,同班还有两位同学和他一起入围。那一年获得一等奖的有郭敬明、郝景芳。
新概念获奖后,刘子超接到一些约稿和作品收入合集出版的邀请,比如书商攒的《第四届新概念获奖者作文新选》,有一次甚至拿了900元稿费,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他用来买书和打口碟,攒了不少古典音乐的碟片。
大学考入北大中文系,似乎是一个文学青年的理想归宿。但刘子超有点后悔自己选了这个专业,因为中文系不教写小说,而是把文学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他宁愿学一门语言,比如俄语、阿拉伯语,对如今的写作会更有益处。于是大学四年刘子超混迹于文学社团,在BBS上发自己的作品,写小说,写诗。当年的社团成员有几位如今仍从事文学工作,茅盾文学奖评委、作家、小说译者。
写小说、写诗,不是毕业后可以选择的工作。如果想要继续写作,非虚构特稿顺理成章是最适合的领域了。但为什么才写了几个月就失去方向了?刘子超也感到很困惑。
在《南都周刊》工作一年后,刘子超又转到同为南方报业旗下的《南方人物周刊》,开始写人物特稿,两年后申请调回北京。他的困惑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还是在想,自己的作品在哪儿?特别是采访完作家或者导演以后,这个问题就会冒出来。”
思来想去,答案始终是一样的:不知道该写什么,有什么是真正值得表达的。于是,刘子超只好迷茫地在业余时间翻译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小说,发在豆瓣上。
二
2011年年中,刘子超完成《ACROSS穿越》创刊号印度的封面故事的两个月后,跳槽到了《GQ》,想着自己的职业困惑也许换个地方会得到解决,来不及让旅行写作的兴趣进一步发酵。
但仍然迷茫。一年之后刘子超辞职,申请到中德媒体使者项目,在德国待了三个月。在欧洲的那个夏天,刘子超去往德国、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意大利几个国家的十几个城市旅行,布达佩斯、维也纳、布拉迪斯拉发、克拉科夫、布拉格,回国之后开始记录这段旅程。他仍然记得动笔的那天是2012年9月3日,两个月时间写了6万字。后来这个部分成为刘子超第一本旅行作品集《午夜降临前抵达》的前半部分:夏。

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的山巅

冬天的意大利的里雅斯特
写完欧洲行记之后,刘子超突然觉得以前那几年的困惑一下解开了,旅行文学可以成为自己的写作方向,自己感兴趣,也能写得好。几个月后,《ACROSS穿越》邀请刘子超回归担任编辑总监,在这份和旅行相关的工作里,个人写作和职业写作不再是相互冲突的关系。
但2013年并不是回归媒体的最佳时点。
刚毕业刚进入媒体行业时,刘子超和那一代的媒体人享受这个行业的全盛时期,媒体永远不缺广告,整个报业集团一年盈利四五个亿。但等到他再度踏回时,整个环境的下坡趋势是肉眼可见的,杂志按期出版,一期比一期更不乐观。一开始大家还寄希望于接下来某个时点就都会好起来吧,像我们对当下疫情的预测一样。但很快坏消息越来越多,减薪、裁员,甚至有几次工资都发不出了。
2016年,《ACROSS穿越》正式停刊。刘子超选择辞职,申请前往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的一个研究项目。牛津大学的项目结束后,刘子超回国,一边旅行一边写作,通常3、4月时进行一次短途,6-10月安排一趟稍微长一点的。在英国的那一年里,刘子超还重译了海明威《流动的盛宴》。他在牛津一家书店里发现了“007之父”伊恩·弗莱明的另类游记《惊异之城》,从英国回来之后将其译成中文版出版。这两本都是特别的旅行文学作品,关于1920年代的巴黎和1950年代的世界大都市,是时间上远方的未知。
小学时的某个暑假,刘子超读了一整个假期的《哈尔罗杰历险记》。
这套书一共14册,讲述了主人公哈尔和罗杰在亚马逊、海底城、食人国不同地方历险的故事,有的单册刘子超甚至读了4、5遍。《哈尔罗杰历险记》的作者威勒德·普赖斯是1900年代的博物学家,受雇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及国家地理协会在世界各地进行科学考察。自文艺复兴以来,博物学家是第一批探索世界,拓展人类认识边界的人。这部历险记也拓展了刘子超关于“远方”的想象。
而第一次对旅行者有概念,是初中时看《鲁滨逊漂流记》。刘子超对旅行者形象的终极认识来源于鲁滨逊。
他觉得鲁滨逊身上有一种开拓者的雄心,同时又兼具冷静、理性和智慧。“这就是我对旅行者的终极想象。这种想象可能是从哈尔罗杰、鲁滨逊、理查德·伯顿、阿拉伯的劳伦斯、罗伯特·拜伦、布鲁斯·查特文、奈保尔这样一路下来的。他们肯定都要去特别艰险的地方,但那些地方又特别丰富。他们独自前往探索,哪怕环境再艰苦恶劣,却依旧能保持内心的骄傲和自觉,所谓grace under pressure。”
旅行确实是充满危险的。
在9年前的那次印度旅行中,车祸带来的影响其实持续了整个行程。尼泊尔的小诊所并没有处理好伤口,进入印度后,刘子超发现伤口只是表面结痂,内部仍然溃烂,甚至有一个小洞。印度尘土多,又脏,每天的行程都是暴走,一天下来伤口总会恶化,他只能买来消毒液、棉花球、绷带早晚自行处理,擦去脓液,用棉花球堵上小洞,再用绷带缠起来。刘子超没有和任何人,包括同事和家人说起这件事,觉得没必要,直到走完40天的行程觉得拿到足够写作素材后,才踏上回程。回北京后刘子超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他如果再晚回来几天,搞不好就要截肢了。
而在他新书《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的旅程里,让人心惊的片段也不少见。2018年刘子超在塔吉克斯坦一段前往帕米尔高原的公路上,两个小时里给警察交了九次钱,每次三美金。有一次因为两个警察实在距离过近,司机摇下窗户真诚地抱怨:“刚交过啦!”警察就挥挥手让他们走了。不久之后刘子超看到这样一条新闻:ISIS开车碾死了4个在塔吉克斯坦骑车旅行的外国人,没死的又下车补了几刀。就在他曾走过的那条路上。
 帕米尔公路
帕米尔公路
但无论如何,旅行作家总是要在路上,不是在路上,就是在去往路上的路上。
去年9月初,刘子超到瑞士领奖,他的作品《乌兹别克斯坦:寻找中亚的失落之心》获得第一届全球真实故事奖(True Story Award)的特别关注奖。领完奖之后他又在欧洲待了两个月,11月回到北京。那是他这大半年来的最后一次出国旅行。
疫情打断了刘子超今年前往黑海和柬埔寨的计划。现在他的最新计划是,先出小区,再做核酸,如果是阴性,再看让不让出北京。

三明治 ️ 刘子超
中国人如何观察世界,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题材
三明治:你是什么时候具体怎么开始意识到,“旅行写作”可以成为自己的写作方向的?
刘子超:应该是《穿越》2011年创刊,我写了创刊号的封面文章“穿越印度的火车之旅”的时候吧。那是我第一次认真进行旅行写作,看了很多书,也有意识地跟印度各个阶层、种姓、职业的人做了很多交谈和采访。体验到一种写“财富人群”时从未有过的喜悦。
那篇两万多字的长文写得特别顺手,然后我就思考是怎么回事。我发现旅行写作其实对作者有几个方面的要求:时间(能不能做有时长达数月的旅行)、体力(每天暴走、颠沛流离,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外语能力(英语流利是必须的,最好还要有别的语言能力)、旅行技巧(旅途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意外、危险有没有办法解决)、知识面(对目的地方方面面的了解和认识)、世界观(怎么观看,放在什么框架里)、采访(如何发现,如何捕捉)、写作(如何处理素材,如何表达)。我不见得是单项得分最高,但可能是综合得分比较高的那种。
三明治:那是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可以把旅行作家当作一份全职职业?旅行也是需要花销的,有没有担心过开支的问题?
刘子超:我一直想成为作家,这是很早就有的想法,但一开始并没有刻意把旅行写作当作职业。当作家总得需要一个起点,我觉得如果我一开始就写小说可能不会有太多优势,这是成长环境和经历决定的,既没有过残酷青春,也没经历过大风大浪。即便工作以后,一天班也没坐过,社交也非常疏离。这样的人生也不能说不值一提,但作为作家出道的确特色不明。但在旅行写作这个小门类里,我比较能发挥自己的特点,就像上面说的——综合得分比较高。
从更大的视角看,中国人如何观察世界,如何与之互动,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题材。以前的中国人没有这样的机会,这是近十几二十年才渐渐开始的潮流。如果未来的中国会成为一个世界性国家,我无法想象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对世界没有做过亲身的梳理、观察、描绘。这个过程英国、美国经历过,我们也会经历。
2016年我从牛津大学回来,媒体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大洗牌,太多人离职转行。当时也担心开支问题,毕竟积蓄有限,但在那种情况下也没有再回媒体的可能性(几乎都在收缩),而彻底转行、当社畜、创业都不适合我——这一点我有自知之明。于是也只有随波逐流,走走看看,从手头能做的事情干起。
三明治:作为自由职业的旅行写作,具体是怎么开始的?
刘子超:离职前一年,2015年,我刚出版了《午夜降临前抵达》,还得了书店文学奖·年度旅行写作。那对我的鼓舞挺大的,让我觉得自己有可能可以靠写作谋生。从牛津回国以后,我一方面梳理手头现有的材料,觉得可以写一本印度和东南亚的集子,另一方面也在考虑写一本更有完整性的作品。回来后去的第一个地方是菲律宾,后来写了《菲律宾跳岛记》,发在了《单读》上。
毕竟在媒体圈摸爬滚打了近十年,还是得到了一定的信任度,只要有作品写出来,总能找到发表的渠道。

缅甸掸邦少女

菲律宾洛博克河谷
三明治:在旅行的过程中还会做一些其他的工作,来维持基本的开销吗?
刘子超:主要是做翻译。这些年也陆续翻译了几本书,现在也依然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翻译工作就像每天去健身房练肌肉,有多大乐趣谈不上,但长期坚持可以维持你的基础脑力,我一般是清晨爬起来先做完今日份的翻译,两个小时左右。
不断离开“此地”,是文学的母题,诗意的所在
三明治:旅行的过程中怎么记录,习惯用手机还是纸笔?
刘子超:我有一个随身携带的笔记本,traveler’s notebook,可以换芯。旅行中随时有发现和想法就会记几笔。比如,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人,他穿着什么衣服,五官有什么特色,都会马上写几笔。这种细节看似没用,但到写作时常常具有唤醒功效。

路上的旅行笔记:亚的斯亚贝巴—哈勒尔
三明治:有没有遇到过回忆时发生断层,或者笔记缺失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的情况?
刘子超:断层什么的可能会发生,虽然我不记得自己发生过,毕竟有记笔记的习惯了。而且发生也没事,记忆也是一种自然筛选的过程。有些事忘了说明可能没那么重要。
三明治:旅行过程中有过物品遗失、被盗的经历吗?
刘子超:旅行中被偷被抢还是很常见的,就当是财富再分配吧。印象里有两次被偷都是在非洲,一次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因为那个地方特别棒,我拍了很多很好的照片,正在走回去的路上编辑朋友圈准备得瑟呢,九宫格刚刚凑满。结果朋友圈还没发出去,手机就被摩托党抢走了。iPhone有定位功能,我赶紧回去用电脑查手机在哪,发现定位在老城的一条小巷里。
第二天白天天一亮我就去了,但进去之后发现阿拉伯古城的小巷完全是一片迷宫,就算你知道你的手机在哪,但周围很多家很多户,你绝不可能进每家每户去问谁把我的手机拿走了。所以一进到那个地方我就想,算了。后来在摩洛哥经常被摸被偷。另外一次丢手机是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也是拿起手机拍了个照,旁边来了几个当地人,一个人吸引你注意力,一个人偷东西,等反应过来的时候手机没了,钱也没了。不过好在没丢过大件行李。
三明治:之前你提到无论旅行多久,都只带一个登机箱和背包,但不同季节要带的东西不同,有什么东西是必带的?
刘子超:我的登机箱是Rimowa的Bolero系列,前面能放mac book air。背包有两个,会根据去的地方换。一个是Freitag PETE(如果主要去城市),一个是功能性更强的AS2OV。必带的就是简单的衣服、洗漱用品、电子产品。冬天大衣肯定要随身穿,行李箱里就不用塞了。
三明治:旅行中会带相机吗?还是只是用手机拍摄记录?
刘子超:重要的旅行会带相机,但现在手机像素也够高了。

印度亨比的一场婚礼
三明治:很多旅行记录都更倾向用影像来表达,尤其现在短视频很火,你考虑过用Vlog的形式来记录吗?会不会觉得旅行文学的空间会被影像挤压?
刘子超:我喜欢精致的东西。用什么形式我并不在乎,只要做得够好。比如我也愿意带团队一起拍旅行纪录片,但如果是很粗糙的东西我就没兴趣了。
三明治:你认为旅行和度假有什么区别?
刘子超:旅行是有共情地探索,度假是解压式地享受。或者简单类比一下:旅行是读书,度假是煲剧。
三明治:旅行在我看来是一个不断离开“此地”的过程,你觉得为什么需要总是离开“此地”?
刘子超:不断离开“此地”就是文学的母题,是诗意的所在。
三明治:有没有计算过目前你的旅行轨迹抵达了多少个国家?有没有还未涉足,但希望未来造访的区域?
刘子超:真的没刻意去算过。但有很多想写的题材,比如“环地中海三部曲”。
1400年过去,中亚依旧如此迷人
三明治:新书《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是提前规划好成书框架再写作的吗?写作持续了多长时间?
刘子超:是先写出一部分之后,停下来思考,结构才慢慢变得清晰起来的。因为我第一次产生写中亚的想法是2010年在霍尔果斯眺望哈萨克一侧的天山,最后一次旅行从中亚回国,则是从哈萨克一侧回到霍尔果斯,等于九年时间形成了一个旅行的圆环。当时的想法是,书从霍尔果斯开始,最后回到霍尔果斯,也形成一个书写的圆环。所以开头和结尾的结构是最早定下来的。中间部分调整过几次,最后决定按照现在的顺序是主要基于叙事的节奏。我希望大家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像听一张交响乐,每一部和每一部之间是有情绪流动的,序幕和尾声又构成呼应。
写作是从2017年9月开始动笔,2019年7月完成初稿,8月二稿,2020年2月又最后重新修订了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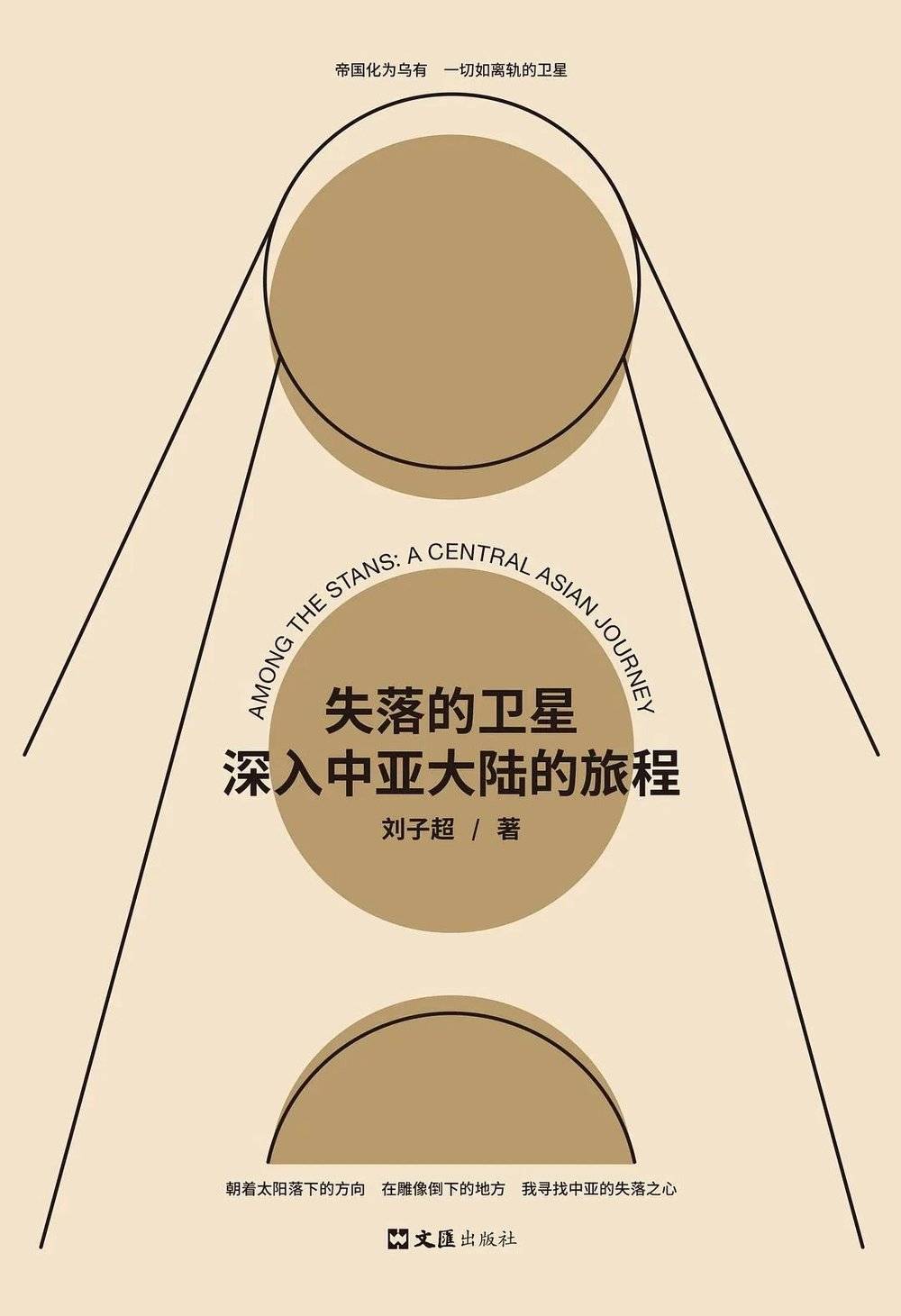
《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封面
三明治:写作跨越了这么长时间,不同的行程在不同时间完成,但最后要系统地组合在一起,这会成为一个问题吗?
刘子超:其实这个没关系的,因为没有人规定旅行必须一次性走完。当你写作时,更重要的是叙述的走向:怎么结构这本书。找到一个合理的结构很重要。
三明治:中亚都是历史、文化、艺术、宗教非常丰厚复杂的地区,看到书的最后最后附上了一些书目,但你实际上看的书是超过这个量的吧,你是怎么把史料信息与行记本身联系在一起的?
刘子超:最后的附录是编辑让我写一些比较有趣味的书目和影像,我接触过的资料肯定远远比这个规模大得多。
史料是你理解这个地方的背景,就好比你写帕米尔高原下的一个村庄,帕米尔高原是这个村子的背景,对你理解这个村子的形成有很大帮助,但你真正要写的还是这个村子里的人和他们的生活。旅行文学如果变成堆砌史料就会变得非常无趣。
因此世界观很重要。先要确定大的思考框架,然后再进入细节,这样就能分清哪些资料是重要的,哪些只需一带而过。

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畔的军事疗养院

哈萨克斯坦努尔苏丹的冬季婚礼

帕米尔高原上的定居点,一个漂亮的小妹妹
三明治:中亚地区的语言很多,书里还写到你也会一些乌兹别克语,是有特意为中亚旅行学习语言吗?
刘子超:是的,旅行中一边走一边学,有机会就练习,所以当时提高很快,回来不用忘得也快。我最后两次去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语到达了此生的“巅峰时刻”,打黑车时能跟司机简单寒暄几句了。之后我就再没付过车钱。因为外国人会说两句乌兹别克语太罕见了,司机无论如何也不肯收我的钱。去年有一次在喀什转机,听到机场广播说维吾尔语,发现还能听懂一些。乌兹别克语和维吾尔语很接近,都是察合台语分出来的。
三明治:中亚这一趟的旅费怎么样?你还申请到了单向街基金会的“水手计划”赞助,足够覆盖支出吗?
刘子超:水手计划赞助了5万块钱,我自己应该花了近10万块吧。也就是说,这本书卖过15000册以后,我才算开始赚钱。
三明治:旅行过程中你怎么解决食物种类有限的问题?有因为饮食而生病的情况吗?
刘子超:中亚传统食物就是馕、抓饭、拉条子、薄皮包子、烤肉这些,到小地方往往就没别的可选了。像阿拉木图、塔什干这样的大城市,还有比较好的俄国菜、格鲁吉亚菜、西餐等。比较幸运的是,我不太有中国胃,可以几个月不吃中餐也没问题。不然旅行会很惨。
在塔什干有一次应该是不小心吃到了一种细菌,导致拉肚子,但又不是吃脏东西吃坏肚子的那种拉肚子。躺了几天,基本不敢吃东西,因为一吃完东西,过15分钟后就会开始拉肚子。最后也没去医院,靠抵抗力自愈了。
三明治:玄奘以后,中国人对中亚的书写几乎很少,在你收集资料的阅读中,还有碰到过其他中国人对中亚的写作吗?你觉得你站在现在的时点和立场去书写中亚,和玄奘书写中亚,是否有经历了漫长时间依然相似的?
刘子超:确实很少碰到中国人对中亚的严肃写作。罗新老师有一篇长文《月光照在阿姆河上》是我唯一读到过的。和玄奘最大的不同,肯定是我们现在对世界认知的深度和广度都已经远远超过那个时代了。他当时是抱着必死的信念去的,因为根本不知道能遇到什么,像黑夜中行路,靠的是一点点摸索。而我显然知道自己不会死,除非出车祸什么的。我也有地图,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相同的是那种执着和探索精神,以及中亚依旧如此迷人。
三明治:接下来还有什么旅行写作计划吗?之前你好像想写俄罗斯,现在进展到哪里了?
刘子超:可能暂时先放一下俄罗斯,虽然已经写了四万多字的克里米亚。主要是这半年来世界发生了太多的事,有点像一场reset,需要通过耐心地阅读重新确立坐标。我自己倒也并不着急。就像打猎一样,开那一枪是很快的,重要的是等待的过程。
题图来自受访者,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依蔓